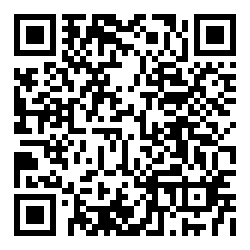从学术思想方面看,古代中国人对“天”或“神”字,以及由这两个字所组成的词的意义的理解,有时直接与哲学上所谓本体(道以及气、理、心等)相关联。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气”、“理”、“心”这些最高思想范畴,理解宗教思想中的“天”或“神”的意义,和学者们以宗教思想中“天”或“神”的意义,理解“道”本体的意义,这两种情况,同时都存在着。
就后者而言,比如,《易传》讲“阴阳不测之谓神”454,这是以宗教思想中的“神”的“不测”性,理解“气”的运动特性。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天理是人们不可离、不可逃、不可抗拒的天命、主宰,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以宗教思想中“神”的主宰权能,理解他形而上学思想中“天理”的普遍必然性和绝对有效性。心学大家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455这是用宗教思想中有一定人格色彩的“精灵”,理解他形而上学思想中“良知”的主体性。
至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气”、“理”、“心”这些表现“道”体的最高思想范畴,理解宗教思想中的“天”或“神”的意义,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宗教思想史上则更为常见。大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天”也指自然、规范,“神”也指神性、良知、精神等。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天”(“神”)有自然实在、本然根据、依存对象几个意义。这几个意义,与古代中国形而上学思想中“气”的意义最为接近。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456“气”就是世界万物中最实在的自然物,它是不以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为转移的独立存在,《周易》的自然气论可以作为典型代表。《周易·系辞传上》说:“乐天知命,故不忧。”晋韩康伯注解说:“顺天之化,故曰乐也。”457所谓“天之化”,实际上是“气”的运动。
即使有意识地突出“天命”的人格色彩,大讲“天命鬼神”的董仲舒,也认为人们对“天意”、“天道”的认识不能离开对阴阳五行之“气”的观察。董仲舒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辩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458在董仲舒那里,“天意”、“天道”,其实与阴阳五行之气紧密相关,人们要见天意、天道,要观“天之志”,必须从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入手。认识到“阳阴入出实虚之处”,就可以认识到“天志”;认识到“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就可以认识到“天道”。如此,所谓“天意”、“天志”、“天道”,都不能离开阴阳五行之气来讨论。关于“天”与气的关系,董仲舒还说得含蓄。明末清初最大的气学家王夫之将“天”的这个意思说得最明确而清楚。他说:“拆着便叫作阴阳五行,有二殊,又有五位;合着便叫作天。”459“天”就是阴阳五行之气,这是自然实在的“天”。
前述古代中国人以有理性色彩的“气”范畴,理解“神”的存在实质,将“神”界定为“人生存之气”460,这是以自然实在意义理解“神”的意义的一个显著实例。
北宋学者张载著《正蒙》,也讲到“神”,比如,他提出“谷之神”、“圣人之神”、“天载之神”、“物性之神”等概念,这些概念的具体意义,还可进一步分析。大体上,张载所谓的“神”,有“气”及其运动性质和功能、“理”及其功能、“心”及其特征和功能三个方面的意义。这里先看第一个意义。
张载认为,“神”是“气”的运动特征和功能。这样的“神”,其实质是“气”。张载说:“气之性本虚与神,则神与性(虚)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又说:“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461张载所谓“神”,一方面指“气”的运动性质。张载自己也明确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神者,太虚妙应之目。”462“良能”,天赋的好的功能。张载肯定鬼神是“气”的运动功能,也是“气”(“太虚”乃“气”之本体)妙合感应的特征。张载所谓“神化”、“神变”等词所说的“神”,其实质就是“气”。
另一方面,在张载那里,“神”也指宇宙运动的动力,当然也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张载说:“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463只有“神”才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也是世界万事万物变化的总动力。根据儒家经典《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观念,世界运动变化的动力,就是阴阳二气相反相成的矛盾。所以,作为宇宙运动动力的“神”,其实质仍然是“气”。
关于鬼神的实质是“气”,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也很赞成。朱熹还进一步分析“气”与鬼、神的具体关系说:“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464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还是人们后天知行活动的本来根据,是现实世界万事万物最初的基础,这个意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表现最突出。这可能和道家对自然无为之“天”观念的突显有关。作为世界万物本然根据的天,集中表现在天性、自然形质等词语上。《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高诱注:“天,性也。”“天”就是指天性。刘向《说苑》也说:“父子之道,天性也。”465后来理学家讲的“天理”,就将“天”的”“性”质意义吸收在内。
古人也将作为本然根据的“天”当作是事物的本真。比如,人们对美的感受、欣赏,就应以这样的本真为极致。这样的本真,在语言上,也用“神”来表示。《易传》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466“几”就是阴阳二气运动转换的关键环节,是形而上的“道”在形而下世界最微妙的表现。这种微妙表现,即是“神”,其实只是“道”的本真表现而已。在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中,有所谓传神之说。元时,书法名家,擅画山水、人物、鞍马、竹石和花鸟的赵孟頫,描述人物绘画传神的方法,说:“传神之法,与画家不同。……将写一神,以纸折作十字,为睛则竖摺之。则可以取眉心、印堂、山根、鼻准、人中、地阁之得其正。横折之,则可以取两眼之得其平。”467艺术评论中所谓“神”,就是事物的本真状态,也可以说就是美本身。
中国古代有学者认为,作为本然根据的天,是人所不可知的。比如,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就说:“皆知其所谓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468在荀子那里,“天”不仅是现实世界本然的根据,而且是现实世界最自然的实在。
虽然“天”的无形没有人知道,但“天”仍然是现实世界,特别是人类生命的依存对象。如《韩诗外传》说:“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469三国时期,吴国的陆凯曾经说“国以民为根”的话,他还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其中提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470这里所谓的“天”,意思就是“本”或“根”,就是指依存对象。老百姓是治国者的依存对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百姓,则国将不国;吃饭问题则是百姓的基本问题,便如韩非子(前280-前233)所谓人是“上不属天,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471的动物,食物是保障人生存的第一位的依存对象,故称之为“天”。
第二,“神”作为形容词,有神奇、珍重、珍贵几个方面的意义,形容词动用,则“神”也可以成为动词。后来理学家所谓“天理”的意义潜藏于其中。神妙、神医、神品等词,是表现“神”这方面意义的常用语词。
《周易·系辞传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晋韩康伯注解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大虚,故两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言变化而称极乎神也。”472韩康伯明言“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并没有其它什么事物使世界运动变化,而是宇宙中的“气”(“理”、“数”是其表现)“自造”如此。故世界万物的运动“无主”,无神。“神”的名称,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气”运动的神妙莫测,所以用“神”这个词来做比喻而已。唐孔颖达完全赞成韩康伯的说法,并为他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疏解。
由此可见,在韩康伯、孔颖达那里,“神”指的就是阴、阳二气变化莫测的神奇性质。
战国末的荀子说:“宝之珍之,神之贵之。”473西汉初的《尔雅·释诂下》说:“神,重也。”474东汉王充著《论衡》,引用当时人的话说:“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475即使道教经典《抱朴子》也说:
“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追风之骏,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476
“夫见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后识焉;见龙而命之曰蛇,非龙之不神也,须蔡墨而后辨焉。”477
“神”指尊重、珍贵,也有因为珍贵,所以尊重的意思。这时,“神”事实上可以作为动词使用。比如,北宋大儒张载说:“圣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于天尔。”478“神其德”,就是珍贵“天德”之义。
珍贵,乃是一种价值评价,价值评价有其价值标准,而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后来宋明理学家断定,“天理”就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系统揭示出“天理”观念的是理学家,在没有系统揭示时,只能是关于“理”的观念。没有自觉的“理”的观念,而直接在价值评价中运用它,这是“日用而不知”的表现。
从“神”的神奇意义看,“不测”者为神,所以“不测”者,即道,更应为神。“道”之为神,比“气”的运动变化的神奇更神奇;从“神”的珍贵意义看,珍贵可谓为“神”,珍贵之所以为珍贵者,珍贵的标准本身,更应为神。标准的神,比因数量多少而为“神”更稳定、准确。在理学家看来,标准的标准,即“天理”,最应为神,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可宝贵者。二程就明确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479如此,神只是“天理”的神妙功能,而“帝”也只是就“天理”主宰世界而言的又一个名称罢了。
以抽象的性理解释“神”的意义,在理学奠基人张载那里,已经露出了端倪。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谓“神”,就有“性”或“理”的意义,也有“性”或“理”的功能的意义。比如,张载提出的“物性之神”这个概念,指的就是“物性”或物理。但张载更重视的不是“物性之神”,而是最一般的性理之神。
张载说:“神,天德。”“神”是天的内在性质或属性,相当于他所谓“天理”。张载还说:“虚明照鉴,神之明也。”480“神”有“明”(光明)的特征,它能够“虚明照鉴”。在理学家看来,天理才是世界上最光明的。如果张载所谓“神”不是“天理”,它便不可能具有“明”的特征。
张载指出:“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481“神”的内涵特征是“兼体而不累”。所谓“兼”指普遍性,与“别”这一特殊性相对而言,“不累”则从反面说“兼”这一普遍性。“神”除非是普遍性的“天理”或者“道”,否则,它不可能具有“兼体而不累”的性质。在另外一处,张载说得更明确:“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482“道”就有“兼体而无累”的性质。所以,所谓“存神”,就只能是人们对于“兼体而不累”的“道”的认识把握。张载说:“知神而后能飨帝飨亲,见易而后能知神。是故不闻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者,末矣。”483所谓“知神”,实际上是认识“性与天道”。张载所说“性与天道”这种“神”,乃是形而上的真理,但又在形而下世界中普遍存在。
张载又说:“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认为“神”是“气之性”,是气之性质或“气”之性质的功能。张载又说:“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484“感”(感应能力、感性能力等)是“性”(人性)的功能,这也是“神”。
古人有关“神”字所蕴含的关于性理的意义,与西方基督宗教关于上帝不可知的神性,关于上帝至真、至善、至美的神性观念,似有可比性。不过,事实上,即使后来大讲“天理”的理学家,揭示出了“天理”的最可珍贵性,也没有将“天理”直接称为“神”,而只是将它称为“道”而已。
第三,“神”有心理、精神意义,良知的意义潜藏在其中。如神色、劳神、凝神、聚精会神等词,其中的“神”,均指人的心理、精神,包含了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欲望等在内。
比如,荀子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杨倞注:“神谓精魂。”485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谈到“道家”(其实主要是黄老之学)关于形神关系的看法,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韦昭注解说:“声气者,神也。枝体者,形也。”486《淮南子》说:“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高诱注:“精神失其所守。”487荀子、司马谈、《淮南子》所谓“神”,也叫作精神,其实都指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欲望等心理活动。东汉王充反对鬼神论,他所谓“神”,也指与人形体相应的精神。王充肯定“神”“必非上帝”488,只是人的心理活动,他称为“精神”。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又说:“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489“精”指的也是他所谓精神。南北朝时期的范缜(约450-约510)继承了王充的思想,明确主张神灭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490的观点。
如果将“神”理解为心理或精神,神灭论是大家都可以赞成的。比如道教经典著作《抱朴子》也可以持神灭主张。它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夫逝者无反期,既朽无生理,达道之士,良所悲矣。”491这时候,所谓“神”只指精神,即人的心理活动能力,而不是书中神仙、鬼神、神明等词所指“神”的意义。
上述“神散”、“神灭”所谓“神”,指的都是人的心理活动,包括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欲望等,现在被人称为精神。它们依赖于人的形体而存在,离开形体就不存在,这是中国古人的共识。而且,心理意义的“神”是古代中国宗教思想中很普遍的观念,比如,祖先神,就是其典型代表。王夫之说:“孝子之事其先,惟求诸其神乎!神则无不浹矣。虚无节者,神所流也;实有节者,神所竟也。于物而见之,于器而见之,于墙屋而见之,于几筵而见之,于绣绘之色而见之,于歌吹考击之声而见之。于彼乎?于此乎?入其庙,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无一之不合于漠,而后与其神浹也。其尤者,则莫甚于仿佛之心,咏叹之旨也。”492“浹”,在古汉语中,有浸渍、透彻、通达、透过、融洽、普遍、遍及几个意义493。“神则无不浹”,当指“神”普遍存在;“与其神浹”,当指祭祀的孝子与祖先神灵融洽相处,乃是人与神和谐统一的状态。王夫之所说的“神”,用科学(主要是心理学)的眼光看,应该是孝子缅怀、追忆祖先,至诚尽孝,结合礼仪、音乐等,让祖先留给后人的记忆重新焕发活力,俨然进入与祖先对话、交流的心理状态,祭祀者在心灵上获得莫大的安慰和满足。心理意义上的“神”,也是有其宗教文化意义的,不必否认。
另一方面,在古人那里,“神”也有良知的意义。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494孟子主张人人都有天赋的“良知”,这就是人的本性。现实的人应该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他在这里所说的“君子”,就是实现了部分人性的、比较理想的人。在孟子看来,“君子”达到了“所存者神”的修养境界,“神”指人的本性或良知,这是君子之所真正存有的核心;“神”也指人本性或良知的“神妙不测”495功能。
孟子以“神”描述人的主体性或本性,对佛教思想的中国化也有一定的启发。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有两个思想要点:一是人人都有佛性说;二是人人都能成佛说。在理论地位上,人人都有佛性说近似孟子人人都固有良知的主张,人人都能成佛说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496说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孟子的良知既然“神”,佛教的“佛性”也未尝不可以用“神”来描述。南北朝时期的慧远就主张“神不灭”论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497其中所谓“神”,就指佛教所谓“法身”基础上人人均有的佛性。梁武帝论证“神不灭”,他所谓“神”,指儒家祭祀的对象,其实就是祖先神灵,相当于人的灵魂。灵魂、神灵,或“法身”,可谓儒家孟子所谓“良知”的人格化。
北宋大儒张载继承孟子君子“所存者神”看法,他所认为的“神”也有主体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后来心学家“良知”或“心”范畴的早期理学渊源。498张载说:“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499他认为,“神”是“清通而不可象”的,而“气”则“散殊而可象”,这就很明确地将“神”和“气”对立起来。那么,这“清通而不可象”的“神”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般人通过学习、修养,达到与“道”为一圣人境界以后所具有的一种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特征,来源于人所认识把握的“性”或“理”的“神”性。张载认为,现实的人一旦“至诚得天”,就成为圣人。圣人具有“神”的性质;圣人可以“存”有、具备、保全“神”,这对于一般人而言,“神”当然是一种精神境界。张载说:“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500如此,“清”“通”而“无碍”,乃是“神”的特征。“清”则不滞于形体,“通”则不受事物阻碍,这应当是主体达到自由的圣人境界才可能具有的特征。
所以,张载说:“高宗梦傅说,先见容貌,此事最神。夫梦不必须圣人然后梦为有理,但天神不间,人入得处便入也。万顷之波与污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来平易,心便神也。若圣人起一欲得灵梦之心,则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圣人心不艰难,所以神也。”501在张载看来,“神”本身没有心。心之所以能够达到“神”的高度,只是“放来平易”,顺应天命,觉悟天理,与天为一。这样,“神”成为“心”的特征或功能,也是圣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其实,从将“神”定位为圣人境界的特征而言,儒家经典《尚书》“乃圣乃神”502之说,已经开始将“神”与“圣”联系起来讨论。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503将“神”明确界定为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圣人的一种“不可知之”特征。据此,张载提出“心本至神”504说,认为人通过人性修养,在认识把握“道”以后,“心”所具有的“至神”特征就可以表现出来。南宋大儒朱熹认为,“圣、神固不可分”,并引用张载的话说:“圣不可知谓神。庄生谬妄,又谓有神人焉。”还引用程颐的话说:“神则圣而不可知,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505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完全按照孟子对“神”的理解,反对道家的“神人”说或道教的“神仙”说,非常明确地将“神”理解为圣人境界的一种特征,比起张载“神”人关系思想而言,悄悄提高了人在“神”面前的地位。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也将“神”界定为“良知”(主体)的特征或功能。他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506根据王阳明的看法,“良知”就是“天理”,就是人的本性,它也是世界的最高主体。就人的学习、修养而言,“良知”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致良知”则是现实的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过程。“良知”的“妙用”就是“神”,这一说法,将“神”看成是“良知”的特征或功能。因为“神”是“良知”的特征或功能,所以,圣人作为人最高精神境界的特征,也可以称为“神”。王阳明实际上从他的心学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圣人境界特征可以称为“神”的问题。这是他在儒家“神”论方面超越程朱理学的地方。
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学思想,在“神”的观念上,也是如此。除了讲“神”就是“气”的运动形态外,王夫之还强调“神”建立在“诚”“几”的基础上,是无形的、难于体验的主体性作用。他说:“故孔子之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诚也;‘六十而耳顺’,几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神也。神无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则神不离乎诚也。”又说:“神者,无为也,形之未形、体之未体者也。则五常百行赅乎诚,蓍龟四体通乎神,诚仁显而神用藏也。”507孔子说“从心所欲不踰矩”,乃是说孔子作为人达到了“心欲”与各种规矩有机统一的高度,这是主体的一种很高的境界。王夫之说“神而不踰其方”,则其所谓“神”,显然是就主体或“良知”而言。因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主体就是“良知”或良心。所以,王夫之谈到心之“本”时,认为诚、几、神三者统一起来,构成“心”的体用层次。其中,“诚”就是人与道合一的状态,而“神者,依诚以凝于人者也”508“神”是达到“诚”境界的人之主体性的凝聚。
“良知”是主体唯心论哲学的最高范畴,黑格尔可谓西方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他所谓绝对精神,与中国儒家的“良知”有接近处:都是宇宙的最高主体。黑格尔用存在、本质、概念这种“正、反、合”公式,逐渐展开绝对精神的辩证进展过程,俨然与中世纪神学所谓“三位一体”相一致,被有些学者批评为神学的残余。这说明,作为形而上的主体,绝对精神或良知,与上帝或神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费尔巴哈说:“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他又进一步揭示人们所谓上帝的实质说:“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的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509形而上学所谓本体与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中西哲学中都有反映。


 张茂泽
张茂泽